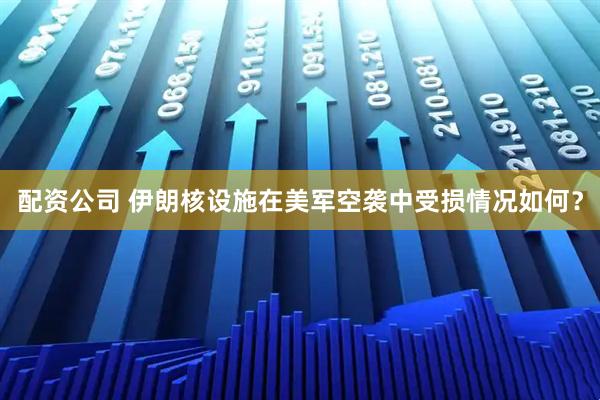在临终之际,我父亲留下了深切的嘱托:让我与庄亲王允禄、大学士鄂尔泰等人共同辅佐皇帝,并且遗诏中指示我将来与他们共同配享太庙。如今,圣上继位之后,依据大行皇帝的遗命,庄亲王允禄、果亲王允礼、大学士鄂尔泰与我一起负责辅政。纵然其中皆为宗室贵胄或满洲勋贵,而我独为汉臣,心中不免自豪。然而华夏配资网,这份荣耀也让我感到莫大的压力。为了不拖累他人,我谦虚地表示,自己更适合担任总理事务的大臣职务。乾隆元年(1736年),皇帝再度派我担任皇子的师傅,同时继续管理翰林院的事务。就在同年二月,皇帝亲自前往景陵祭拜,而我与其他几位老臣被留在京城,继续负责国家的政务。
自此之后,每当皇帝巡幸外地,我便留守京城,代为处理事务。初时,皇帝对我信任如其祖父和父亲一般,常常让我参与决策,并在夜晚安排我留宿紫禁城,给了我相当大的权力。我不仅负责管理朝政,还承担了科举考试的工作,选拔人才,考察官员。我虽忙于政务,但从未忘记父亲的教诲,坚持读书,因此我同时荣膺了雍乾两代的皇子师傅,且担任了《清圣祖实录》、《明史》、《大清会典》以及其他重要典籍的总裁官。
展开剩余81%乾隆二年十一月,我被授予总理事务大臣的职务,特命进封三等伯爵,并赐号“勤宣”。至乾隆三年,皇帝亲自视察国子监并举行古礼“三老五更”,我认为此礼不合时宜,特意上疏指出。当时我几次提出与皇帝不同的意见,虽然没有引起皇帝的怨恼,反而继续赐封我为伯爵。这在汉臣中极为少见,皇帝对我格外恩宠。然而,年事已高的我,逐渐暴露出年轻时的缺点:固执、易激动,这使得我与皇帝之间逐渐产生了裂痕。这些问题也正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积累的。
乾隆十年四月,我的搭档鄂尔泰去世,满洲大臣讷亲取而代之,且排名在我之前。虽然我勉强同意讷亲居于内阁首位,但心中却颇感不平。毕竟,鄂尔泰与我共事多年,尽管有时政见不同,但彼此相互尊重,虽有分歧,但最终还是可以和睦相处。然而,讷亲这个新晋的大臣竟然排在我前面,令我不甘。为了平衡各方,皇帝下令:“嗣后内阁行走列名,讷亲在前;吏部行走列名,我在前。”虽然表面上看是平衡,但实际上却加深了我们之间的矛盾,朝堂上也因此风起云涌,明争暗斗,互不服气。
我与鄂尔泰共事多年,性格上虽有差异,却始终在一起工作。鄂尔泰有时会犯错,我会毫不客气地批评他,这导致朝中形成了“鄂党”与“张党”之争,许多汉官站在我这一边。这种党派纷争使得朝政不稳,皇帝也逐渐对我产生了不满。直到乾隆十三年正月,我因年老多病,提出辞职。皇帝下旨慰留我,表示我既受两朝恩宠,又奉了先帝遗命,将来配享太庙,怎么能就此归田休养呢?这一番话令我心中感到一些不满,觉得皇帝与圣祖爷不同,圣祖爷曾两度支持父亲辞官回乡,而如今轮到我,似乎没有同样的理解。
仅过了一年多,皇帝又命我照宋代文彦博旧例,定期议事。然而,我的健康状况已无法承受如此繁重的工作,遂再次向皇帝请求离职。皇帝暂时批准,允许我保留原职,且赐诗三篇慰藉。我若能心存感激,恭敬回谢,也许一切不会变得如此糟糕。可惜,在与皇帝会面时,我仍然提出了不该提的要求,表示担忧自己在死后无法享受太高的待遇,甚至外界也有类似的议论。皇帝愤怒之下,仍然为我拟定了手诏,重申圣祖的遗命,并赐诗安慰我。尽管皇帝如此处理,我却再一次犯了忌讳。
次日早晨,我没有亲自前往谢恩,而是委托儿子张若澄代我入宫,结果皇帝因我未亲自谢恩而大为不满,命令我明白回奏。当时,傅恒和汪由敦为传旨大臣,尚未将旨意下达,翌日黎明,我匆匆赶赴内廷向皇帝谢恩。皇帝愈发不快,认为这是军机大臣泄漏消息所致,责罚了汪由敦。接着,廷臣商议,决定剥夺我的官爵,取消配享太庙的优待。此事过后,我心生悔意,再也不敢提起之前的请求。然而,乾隆十五年,我再次触犯皇上,当时,皇帝的嫡长子永璜早逝,皇帝心情沉重,我却不自量力,再度提出了当初的要求。
皇帝怒不可遏,最终命我自己决定是否配享太庙,并且通过大学士和九卿的议定,取消了我的配享资格,并免除我的治罪。之后,我被允许回乡。然而,不久后,由于我的门生四川学政朱筌的犯罪案件,我又被牵连其中,被命令缴回所有赐物。此时,我深感悔恨,真心后悔自己曾如此轻率地向皇帝提出不该提出的要求。
回想当年刚入仕途时,我是多么的谨慎与自律。记得第一次主持会试时,有门生向我敬礼,我不仅没有接受,还以前明大臣左光斗为例,教育他们要洁身自好。我在处理政务时,也常常提出改进奏折制度,以防问题发生。对我的孩子们,我始终强调要小心谨慎,甚至在我的儿子张若霭考中探花时,我也主动劝他将位置让给其他有才之人。可如今,我却走到如此田地,真是荒唐至极。算了,往事如烟,我只能祈愿皇帝不要再因我之过错而责罚我的家人。至于张家,也算是有始有终,时至今日,已不复往昔荣耀。
发布于:天津市智慧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